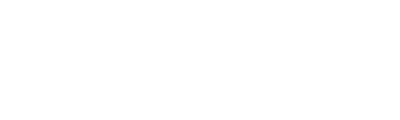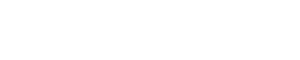——于渌院士,金奎娟研究员在2011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更新于2011-10-08
于渌院士,金奎娟研究员在2011年开学典礼暨入所教育上的讲话
提要:
专题报告(一),主讲:于渌院士
专题报告(二),主讲:金奎娟研究员
(一)
(根据于渌院士讲话整理)
从新兵到老兵--五十年的变迁 于 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研究生部的李老师让我做个半小时的报告,讲点什么呢?我想了一下,今年正好是我入所50年,来所时,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年纪,24岁。就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物理所经历的事情,也许对同学们有一点参考作用。我想说这么几件事:新兵的尝试、文革中的机遇、老兵的追求、变和不变。
‘新兵的尝试’。
1961年我从前苏联的哈尔科夫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物理所工作, 10月份到所里报到。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我没有机会读研究生,也没有博士学位:当时苏联大学的导师很希望我回去读研究生,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就不能回去读书了。不仅回不去,后来17年也不能出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有改变。上世纪的1960、61、62年,大家可能听老人说过,各方面都困难。我分到物理所时,住在家属宿舍,里外一个套间,每间屋有四张双人立床,能住16个人,当时的室领导,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秘书,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有十二、三个人。粮食定量是32斤,为了顶饱,拿1斤粮票换5斤白薯。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劲头很大。当时我被分到理论室,当时的室主任是李荫远先生,现在还健在,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他对年轻人非常提挈。他原来希望我和他一起工作,后来发现我的兴趣在别的方面,就要我新开一个课题,研究超导,还给我分了2人,让我当课题组长。大家可以想象,大学刚毕业就当课题组长,这个担子很重。当时氛围非常好,大家想学东西,想做事情。室里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是新的研究方向,没有老先生来指导,大家就互教互学,看文章互相讲。我当时负责组织学术报告,每周的报告表排得满满的,一讲就是半天。讲的人不一定全都稿清楚了,但通过大家提问,反复讨论,逐渐把事情搞懂,甚至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互教互学的环境中,大家进步很快,我自己也很有收获,不到两年就开始写文章。这就是当时在物理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报告时的ppt)。这篇文章是63年7月份投稿,65年刊登出来的,下面我简单讲一下它的背景。
超导是昂内斯1911年发现的,他1913年拿到了诺贝尔奖,因为他首次将氦液化,也因为超导的发现。又经过46年许多代物理学家的努力,1957年超导的微观理论才建立。又隔了15年,巴丁、库柏和施里弗三人得了诺贝尔奖。超导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抗磁效应,伦敦兄弟提出了一组唯象方程,既能描述零电阻,又能描述完全抗磁性。学过量子力学,知道如果算电流的期待值,它有两项,一项是‘顺磁项’,一项是‘抗磁项’,在通常金属中这两项差不多,互相抵消,还剩下点弱的抗磁,叫‘朗道抗磁’,它是泡利顺磁数值的三分之一,符号相反。弗里茨•伦敦假定,超导体波函数具有“刚性”,使得顺磁项等于零,只剩下抗磁项,就是第二个伦敦方程。后来巴丁意识到,如果体系的激发谱有能隙,波函数就会有“刚性”。通过杨振宁先生推荐,库柏参加了巴丁的团队,不久发现一个定理:在费米面上存在任意弱的净吸引作用时,会形成电子束缚态,‘库柏对’,它的束缚能,就是巴丁想要的能隙。很快,施里弗想出了一个波函数,就是著名的 BCS超导基态波函数。问题是解决了,但诺贝尔奖晚了15年,原因是这里涉及很重要的‘对称破缺’概念,很多人,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些老先生,反对这个事。库柏对是由波矢为k和自旋向上的电子,与-k和自旋向下的电子组成的,尊从时间反演对称,安德孙195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非磁性的杂质对超导电性影响不大,时间反演态还可组成库柏对。后来阿布里科索夫和哥尔科夫发表文章指出,如果掺磁性杂质,就会使能隙减小,转变温度降低,因为磁性杂质破坏时间反演对称。他们是用微扰论做的,有没有更重要的影响呢?我当时想有一个很直观的图像:超导体原来是金属,超导转变打开能隙,和半导体类似。半导体引入杂质后,可形成束缚能级,超导体加顺磁杂质,是否也会形成束缚能级?仔细算一算,果然如此,用的是广义自洽场方法。这个计算是一个大的习题,不很复杂,后面我又做了些其他的计算,为了和电磁吸收及隧道实验比较。很久以后才知道,日本的科学家Shiba和前苏联科学家Rusinov 也做了类似的计算,但他们晚些,分别是1968 和1969。这个计算结果比较难验证,因为束缚能级距离能隙边缘非常近,束缚态的波函数比较延展,不容易观察到。直到1981年才在隧道谱中观察到这个束缚态,1997年在STM的实验中被直接‘看见’。我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练习,做完也就完了。1994年去 Los Alamos访问,见到 A. Balatsky,一个俄国学者,他正在研究杂质对高温超导体的影响。我说30年前,做过这个练习,计算含顺磁杂质超导体中的束缚态,他看到原文后就帮着宣传,50年前的文章,从这以后,引文开始多起来。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时虽然没有人指导,但凭借年轻人的激情和追求,通过互教互学,敢于做一些事情,可以做一些事情。
‘文革中的机遇’。
文化大革命当中,绝大部分科研工作都停了。1969年我被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回所后,理论室解散了,去了五室,做超导实验。后来郝柏林重新组织了计算机和理论组,在磁学室。建组的直接原因是当时打破封锁,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小型计算机,叫Nova 1200。名义上是进口一个‘武田理研’的数字电压表,实际上是因为带了这个计算机。后来组织了一个队伍,先是程序和软件人员,后来又加上硬件人员,来‘剖析’这个计算机。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小型计算机的发展从中受益良多。在这个过程中,还碰上一个机遇。杨振宁先生1971年首次到国内访问,1972年再次访问。第一次毛主席见了他,第二次周总理见了他。总理见他的时候,周培源先生在场,主要谈基础研究如何重要。周培源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整版的文章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当时意识到,这是做基础研究的一个机会,就在剖析计算机的同时去图书馆去看文章。这一看大吃一惊!就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际上在相变和临界现象理论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大家在高中物理和普通物理课程中学过范德瓦耳斯的气体状态方程,它是描述相变现象最早的平均场理论,后来又以不同的形式被多次‘重新发现’过。朗道把它归结成非常简洁的理论表述:在相变点附近可以把自由能按照序参量展开, 再作一些物理上合理的假定,就可以推算出描述相变点临界行为的“临界指数”。通常平均场理论给出的结果相当好,因为它往往能抓住物理本质。可是在相变和临界现象里,平均场理论彻底失败了。60年代,实验已经做得比较精确,在实验精度范围内测量结果与平均场理论预言完全不同。经过许多科学家的努力,在总结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标度律”、“普适性”等,逐渐形成了相变新理论的基础, 1971年,一位搞场论的物理学家Ken Wilson采用“重正化群”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先把高动量、小尺度的涨落积掉,推导出描述较大尺度上涨落行为的有效哈密顿量,再作标度变换,退回原来尺度。这一系列变换在‘参数空间’构成‘重正化群’,根据它在‘不动点(对应物理上的临界点)’附近的展开可以算出临界指数,与实验完全符合,并从理论上认证了“标度律”、“普适性”等重要概念。当时我们跟外面隔绝,没有任何交流,但幸好,幸好,文革期间物理所图书馆订的杂志没有停,我们把能找到的杂志都看了,又是采用互教互学的办法,在组里讲这些东西。讲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有几十次吧,讲稿叠起来的厚度有好几十厘米。从这些讲稿中郝柏林和我提炼出一些内容,先在《物理》上写了三篇短文,后来扩充成一本小书,叫《相变与临界现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最近又再版了一次,陈晓松教授也参与了。
我们当时一边读人家的文章,一边也自己做计算.。相变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平均场理论在四维以上的空间才正确,可以把4-空间维数当成小参量,发展计算临界指数的方法。我与郝柏林合作,根据重正化群的基本思想,利用费曼图解方法做了这个计算,算到临界指数对这个小参量展开的三阶。这个计算比较复杂,比第一个工作复杂得多,有个积分就算了两个月,当时用A3纸当算稿,放在一起有好几十公分厚。算完以后很开心,但很快又有点沮丧,因为在图书馆新收到的杂志上看到了Edouard Brezin和他的同事用场论中的Callan-Symanzik 方程也做了这个计算,结果是一样的,但方法不同。 他们的文章总共2页,没有任何推导。我们想既然是独立地进行了计算,方法不同,还是把它发表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们的文章是73年9月份出版,收到杂志肯定要晚,而我们的文章是73年12月投的稿,直到75年才出版,连英文标题和摘要都没有。这件事还是有些后果的。1975年美国物理学会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到中国来调查文革期间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的都是些‘大牌’,有马丁、施里弗、做非线性光学的 Bloembergen, 做超导隧道效应的 Giaever 等 (这四位都是诺奖得主)。美国人一般都比较自由散漫,这次非常特别,他们在来之前就在日本开了预备会,完了以后还专门开了总结会,最后写了一本蓝皮书,我们图书馆有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那里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经历的一些事情,也记录了我们与他们交流的情况。这对后来我们重回国际学术界起了一些作用,包括1978年到比利时参加著名的Solvey会议,1979-81年去美国访问,以及后来邀请我到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ICTP)做研究和负责凝聚态物理部的工作十多年。我想说物理所是个很好的做学问的地方,长期形成的好氛围扎下了根,即使受到干扰,还有一定的‘免疫力’,一有机会,这种氛围就能恢复,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老兵的追求’。
我今年74岁,但是对于科学上的东西还很感兴趣。我自己跟一些与我同龄的同事和国外的一些同行还在研究一些自己感觉困扰的问题。我最困扰的问题,就是高温超导。已经25年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理解。最大的难题并不是为什么Tc这么高,什么是‘超级胶水’,更重要的是正常态就不能用朗道的费米液体理论来描述。一直有很多理论上的尝试,我们也在尝试当中。这里有很多的现象,比如线性电阻啊, ‘暗熵’啊,等等。我们的尝试用规范场的框架,基本思想是安德孙提出来的,从莫特绝缘体出发。用直观的图像,在这样的体系里,自旋和电荷是分离的,空穴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粒子,而是一个‘复合粒子’,是一个spinon和一个holon,中间用规范场把它联系起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发现这个理论框架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一些性质,如赝能隙、金属-绝缘体转换等。最近我们比较高兴,又在这个框架里提出一个三部曲,来解释超导怎么出现的,先是holon配对,又诱导出spinon配对,它们合起来变成空穴对,最后非相干的空穴对关联起来,形成超导。我想强调一下,这仅仅是个尝试,是许多种尝试之一。我想说的是,虽然年龄大了,对科学问题的兴趣不减。
‘变和不变’。
我开始讲到61年来所的一些情况,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开放了,有互联网,有出去交流的机会。我们研究工作的体量和水平也完全不一样了。前几天AIP的副总裁讲了一件事我原来不知道。美国AIP负责出版好几种期刊,投稿最多的是中国大陆,投稿量占20%,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投稿量,APS 出版的期刊也类似。当然,我们文章发表的量没有那么多,发表的比例低一些,但相对于原有基础是剧烈的变化。实事求是地说,很多方面,包括实验设备、经费支持等都有很大改善。但是,对于做学问来说也有新的问题,诱惑多了,容易产生浮躁。我今天最后想和同学们讲的,就在这个变的当中要有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想做科学的话,必须要靠不变的东西,我自己感觉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激情,它开始是由好奇心引起的,但是光有好奇心不够,要有持续的激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机遇,它不是到处都有的,但要准备好,有机遇的时候才能抓住。第三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要执着,想清楚了,要做这件事情,就不要放弃。搞科学比较清苦,但有一种乐趣,别的行当很难有,当你第一个弄明白一个问题,认识到别人没有认识到的事情时,那种乐趣和满足感是很很特别的。
祝愿大家学有所成!谢谢大家!
(二)
(根据金奎娟研究员讲话整理)
大家早上好!
我是第一次做这样学术报告之外的报告,前几天我接到研究生部的委托之后,我还是想了想,主要(想)和大家讲什么。以我自身的感受为例,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当初做学生的感受,尤其是这些感受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诠释,最后我可能想和大家说一点题外话,我感受可能从两个方面来讲。
大概结合我的经历,主要是我做学生的感受,我是师从杨国祯院士,当时是杨国祯研究员,99年杨老师被评为院士,还有一个辅助的导师是潘少华研究员。在讲的过程中我会结合我现在做导师的感受,来回头去看看,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和一个导师的角度,学术成长旅途的分析会不太一样。这是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报告时的ppt),物理所,我们那届博士生26个人,只有我一个女生,(刚)入学的时候是两个(女生),然后第二个女生很快就嫁给了老外,就出国了,所以我就变得很孤单。我们这一拨学生的关系比较密切。当初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有三种老板,但是其实我回过头,即便是一个导师,可能对不同的学生,他的指导方式也无外乎这三种。那么,哪三种呢?第一种是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题目,告诉你这个题目是肯定能做出来的,但是通常这类题目比较小。就是基本上讲,题目比成一个兔子的话,那么就给你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这片森林第19颗树下有兔子,你去打吧,打的时候还是要克服一些具体的困难,但相对来说就要简单;第二种方式就是给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说西北的方向可能有兔子,这个是存在有一点风险,它也可能没有,要搜索的面就大了,也可能增加了难度;第三种就更加宽泛了,这片森林应该有兔子,在哪?自己找吧!对于第一种,非常保险也省力,但是弊端就是兔子可能不太大。那你想,那么容易的事,别人也能做。轮到你的时候,骨头里就啃的没什么肉了,有肉也就剩点肉丝,你再吃吃力就把它啃了。所以呢,第二种是一个中等的培训强度。那第一种比较简单,如果一直做这样的工作,作为一个博士生,你毕业之后,你怎样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去指导学生?这其实是有难度的。我今天的感受,我不知道别人,在我这,我可能更多的是给特别具体的题目,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不管,那真可能(学生)半年没东西,所以呢,你比他还着急,你可能做的指导特别具体,有什么问题都跟他,但事实上我自身的感受,就是结合我自身的成长经历,我觉得很多困难事实上是你要坐得住,然后自己去克服的。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大家急于要出东西,学生肯花在这方面的时间也肯定没那么多。所以,种种原因导致大多数都是第一种和第二种。那么最后这种呢,难度大,有风险,甚至有毕不了业的风险。我上面有一级的学生在物理所做了6年或7年,没有毕业,博士应该是3年的,好处是你可能收获是意外的,它可能是巨大的。
我先说一下我曾经感受到的,这个(是)痛苦迷茫和黑暗,黑暗到什么程度呢?刚来物理所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报告都听不懂,甚至导师跟你说的话你都听不懂,师兄说的话你也不太听得懂。然后呢,你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有一天,上午站在窗口看到楼下有工人在铺路,铺门前的那条小路,然后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再往窗外一看,这条路已经铺出去好长了,当时就一个感觉,想做个铺路工,就觉得这真有成效啊!你做办公室,你看文献,坐了一天,脑袋里还是一团浆糊,这种黑暗有多黑暗?我去查了我的日记,还真查到了。我是92年9月份入学,由于种种原因,在93年6月份调了方向,我是从原子物理调到了凝聚态和光学。在调了方向四个月的时候,我题了这首诗(报告时的ppt),就是在特别迷惘的时候,我把它记到我的日记里了,然后写了这首诗,贴到了我们宿舍的墙上。我当时的舍友是心理学的博士生,号称是她们心理学界第三位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我两一起痛苦,她师姐当初答辩的时候就直接被挂在白板上了,就什么意思呢,就被别人问住了,答不上来,然后立马就哭了,结果可想而知,学位没有拿到。所以,你想,在那种环境的压力之下,她比我高一届,我觉得痛苦也不比我小,有这么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黑暗迷茫,你基本上又自嘲又共勉。我昨天还想了一下107应该是我住的宿舍房号,但这个我是按照我日记原版抄下来的,所以呢我这首诗挂在房间我们两一起共勉,这个时间就是我转方向四个月的时候,从原子分子物理到凝聚态、光学的调整,可想而知我的压力有多大。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讲这段呢?我就希望大家未来在物理所的这段,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能想到,金奎娟当初也这样,就能够看到点希望和曙光。当时的条件,刚才于先生也讲了,当时条件还是蛮艰苦的,我在A楼的418房间,阳面,一个特别不透气的房间,没有空调,整个夏天跟蒸笼一模一样,没有网络,当然好处是没有诱惑。但是呢,坏处是机时的冲突,当初我刚看到些曙光的时候,我师兄正在用计算机,发生机时的冲突,我不能用,就那一台计算机,我在楼道里走啊,跟一头困兽一样,急啊,就觉得我时间浪费了,可惜啊。我拿我的学生为例,我就特别不理解,每个学生有一台电脑,你去看,晚上很多都在打游戏,看电影,我就特别不理解,这种状态,时间浪费是自己的,怎么就不心疼呢!当然确实时代不一样了。另外读文献,就像于先生讲的,基本上所有文献要到图书馆去读,复印,拿回来,基本上在图书馆――办公室。
这样,我基本上在转了方向之后,导师给我的题目就属于最后一种。当时做的是什么呢?Fano效应,是在原子分子由Fano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一个分立态和连续态重叠发生耦合的时候,它的吸收谱会出现一个非对称的这个线型。我正好从原子分子转到凝聚态,导师就觉得这样的题目很适合我,(导师说)你看看,半导体量子阱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效应?如果有,它会在什么样的体系下发生,它是由什么和什么耦合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宽泛的题目,我虽然从原子分子转过来,但我并不知道有这个效应,基本上从最早的推导Fano效应――原子分子所有推导开始,把所有推导都做一遍后,基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明白他的工作了。但是怎么样推广应用到半导体量子阱体系里?当然我在导师的帮助下,导师帮我限定了一些文献,读下来的结果,我发现在半导体里有人做到了电声耦合,因为声子是个分立态,电子是个连续谱的话,那么可以出一些效应,慢慢的我就看到了一点曙光。因为量子阱里是分立的,上面有连续的,那么那个连续态和声子的分立态会不会出耦合效应?基本上思路清晰,困难是所有的都要重头推起,那么这里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具体困难。基本上就是这样,即便导师不要说交给你个宽泛的题目,即使是具体的题目也一定会遇到很多具体的困难要解决,那么能不能实现,到现在就没人知道能不能做成,那么也就到了93年的年底,杨老师开始着急,担心(我)做不出来,想给我换一个具体树下的兔子,想帮我换个题目――光学的相位恢复的事情,大概讲了一下午。我跟杨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心里其实有点数了,您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做不出来我再换题目,这样坚持下来,我说的是93年年底的事情,到94年的年初,就看到了曙光,94年的年初我们就投了第一篇PRB的文章,后来被接收。以前物理所PRB的产量肯定不如现在物理所PRL的产量,大概一年20篇左右,所以这样的一项工作就基本心里有底,毕业应该没问题了。
所有的事情你都一点一点去做了,你会受到别的启发,当初的工作设计基本上参照半导体做的是拉曼谱,那么多有关拉曼的工作我都要做一遍,但做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其实吸收谱里能做这个事,也就是量子阱往它的连续态跃迁的时候,那么由于这个电声耦合作用,也会发生吸收谱一些不一样,一些共振效应,就叫Fano共振。所以接下来在95年的时候,我们又把它推广到吸收谱,第二篇PRB又被接收了。然后组里讨论,杨老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实验上能够实现。因此,安排组织力量去做了拉曼谱的实验,在做拉曼谱实验的时候,其实还会遇到困难,所以主持拉曼谱实验工作的陈正豪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在超晶格中实现?大家知道,量子阱就是一个阱,超晶格是多个阱耦合,也许信号强就能观察到。这样事实上往超晶格上推广,又要重新设计结构,又要重新去寻找这个路径,但是呢这个最后也是实现了的。这样一个理论和实验的工作,这样一个配合,最后又发了一系列的文章,这样一个过程和于老师讲的其实是一样,你能坚持下来,能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兴趣和好奇心!它是一个原动力,你一定要弄明白这件事,一定要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一定要知道下面是可以发生什么?这个原动力和好奇心比什么都重要。那么当然接下来所有的这个荣誉直接就过来了,95、96年的时候,也是因为Fano效应这么一系列的工作,那么我获得首届科学院亿利达奖学金的一等奖和院长奖学金的特等奖,然后留所工作,之后又获得饶毓泰基础光学一等奖。
那么97年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去美国也和我这个工作是相关的。当时一个挪威的教授来物理所访问,想招博士后,有人把我推荐给他,事实上我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但是他没直接跟我说,他和介绍我的王恩哥老师说他这次在中国遇到的,觉得这是个能力最强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挪威的评审机制,最后引入了一个挪威人来做。这个机会我失之交臂,但是紧接着G. D. Mahan,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去他那访问,要收博士后,他就直接把我推荐给他了,然后给我写的一封信,说G. D. Mahan要招博士后,我已经向他提了你的名字,你直接跟他联系。我当时就在ICTP,就在当时于禄院士做主任的,意大利的理论中心,我是短期在那做一个月,就在那的时候,接到了这样一封email,接着我就和G. D. Mahan联系,email发出去的第二天,G. D. Mahan直接就给了offer。就说尽快过来。到了美国之后,一切的历史又重演了,我相当于从光学的领域,因为我做光跃迁嘛,一下又到了做表面,然后又开始了迷惘和黑暗,所有的事情,当然G. D. Mahan也很忙,我开始整天追着他问问题,搞的他…….。对,他又去瑞典出差2个月,3个月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过了几个月的黑暗迷惘了,找不到办法,自己弄吧,和张振宇教授合作,做了一个量子效应的事情,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我给了他结果,他很高兴,那个工作后来就投给PRL,然后也是接收了。接着是做了第二个,也是在做第一个工作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工作的想法,接下来做了第二个,结尾的时候我从他那离开,我想他从开始的恼火到后来,也比较满意了。我在后来再跟他问问题时,他就特别喜欢跟我开玩笑,就经常说一句话――那是你应该告诉我的,那是你应该告诉我答案的。这时,就觉得已经达到平等可交流的(境界)。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被称为是凝聚态物理的圣经,他将在今年秋的10月底到我这里来访问,现在已经七十二、三了,如果同学们感兴趣,也可以到我这来听报告,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也是回来这么多年之后才敢邀请他。
总结一下,其实所有这一块,你的感觉就是你未来的路就是用你这几年的辛苦来铺设的。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这几年非常重要。你把握住这几年的机会,也就这几年,你这几年做好了,你的前途就光明了,所有的机会都来了,你做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想,什么拿奖啊,什么都没想,就想做,做完了就发现,什么都有了。这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感受。
最后想说一点题外话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学生都是好学生,但是很多事情呢,你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对你提醒过。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比如说父母是农民的,父母是工人的,可能父母是高知的并不多。所以呢,可能我们在家庭里受到的可能并没有足够,很多东西是你要出来去学的。你看别人行为方式,自己去补充的。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个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些东西你要慢慢来感悟。大家来这里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那么你的道德修养和行为礼仪应该到了一个很好的程度,但是我发现不是。就比如,前几年我到物理所餐厅排队,在新生入所的时候,一个人哗一声就冲过来了,两个人估计是朋友,在谈笑,我说:对不起,我们在排队,然后那个女生非常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把我也弄火了。我说:你是物理所的吗?她说,我们就是物理所的!非常理直气壮,我们为什么问这个话?因为我不相信物理所的学生会这样,她说我们就是物理所的,然后我问,你导师是谁啊?你管我导师是谁!然后我说,如果你都不能好好地做人,还做什么学问啊?所以这件事啊,我是当时确实很气愤。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没关系,你这个态度很激火,当时研究生部王松涛在管,我给王松涛老师直接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入所教育能不能做一下教育,虽然我不认为这是在博士生应该的入所教育,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正好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想把有些事情拿出来一起说。其实,做人和(同时)做学问有多么重要!我用几个例子说明――其实有时候做人比做学问更加重要。有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些行为规范,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件事本来是我的一件私事,我在外面出差,当时我儿子是上了小学4年级,给他报了一个新东方的班,挺远的,我就给我一个学生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带他骑车走一遍。我的意思是带他骑车走一遍,他就认识路了。我学生跟我说没问题。然后这件事就这么做了,我就谢谢。过了一个月,我在跟我儿子怎么说起路的时候,我说就是你们去那的那条路,他说,我不走那条路,我走这条路,我发现他在逆行!当然我在批评教育了他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我要说一下,然后我在和学生讨论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讲,我说这是我的一件私事,我请学生做的很不应该做的事,完全靠私人交情做的事,但是我一定要拿出来讲,你们都是受了这么高等的教育了,如果你们都不能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说你们,你们能带着一个小学生都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将来都是要有孩子的,你们会这么样去教育你们的子女?那你可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最起码的!我学生说,我不知道自行车不能逆行,他说我只知道汽车不能走那边。我一下想起来,沂蒙山区出来的孩子!所以我就说不是,孩子都是好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提醒。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提醒。还有一次也是新生入学,我乘电梯,电梯一开,哗,冲进来一个女生,里面的人没出去呢!我一看,我们组新来的女学生,当天下午,正好是新生欢迎会,我们组开的,座谈会,我把这件事讲了,但是我没点名,我也没说早晨我遇见这件事,我说大家应该遵守行为规范,电梯开的时候,你让电梯里面的人先出来你再进来,起码的礼貌,对吧。然后呢,很有效果,我们光物理实验室在工会组织活动的时候,我们实验室90多个学生,工会组织活动的时候,工会老师就讲,你们组学生真好,但是有的组的学生真的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大客车上车,你们组学生去了,一律只坐在后面,就有个别组的学生,上来就抢座位,把前面全抢了,有老师,老师那么大岁数了,要往后走。同学们,你们想想,这合适吗?你就为了坐在前面?所以我觉得报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些基本的素质修养属于这个小节的方面,我还是觉得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这是最基本的了。也是我们组的学生,打电话,办公室里坐着5、6个学生,旁若无人,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允许的,组会上的时候我一定会说的,当然我不会点名,这样的现象是不可以的,顾及一下别人。那么包括你出门的时候,如果后面有人的时候,别让人家走到门口,啪的把人家打在那了,这都是最起码的。但是就是没有人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所以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的时候,沃德要招一个博士后,然后来应聘的是个中国人,他在美国已经待了三年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一个午餐会,那天讲报告的正好是我老板――杰瑞.马汉,杰瑞马汉在上面讲,屋子里有30个人左右,大家都在吃着东西,没有人发出声音,只有我们应聘的博士后发出极大的声音,其实很简单,你闭着嘴嚼啊,但是,就是你觉得,你真替中国人觉得脸红,他肯定一点都没有意识。人家在作报告,满屋子都听他咀嚼的声音,就你真不好意思,当然结果可想而知,这个人没有被聘用。其实别人和你work,是不是很愉快,是由这些小节来组成,宗旨还是一句话,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你如果是一个别人相处很愉快的,这个在职场是非常重要的,最后预祝大家在物理所的日子都非常精彩!谢谢!